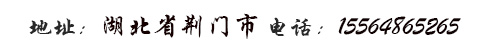慎志浩圣地亚哥的天空
|
圣地亚哥的天空 ——读乌拉圭小说《破角的春天》 文: 慎志浩 圣地亚哥是《破角的春天》里的主人公。打开小说,我看到他的天空只是架在四面墙上的屋顶。 一 作者:贝内德蒂 “今晚我独自一人。我的室友在医务室。他人不错。但偶尔一个人待着也不赖。我可以更好的思考……” 《破角的春天》第一章,就从异议人士圣地亚哥给妻子格蕾西拉写信开始。这一章的题目叫“在墙内(今晚我独自一人)”。 也许你已经知道,这堵墙就是监狱的墙。你不知道的是这座监狱的名字被命名为“自由”。 《破角的春天》的故事就是围绕圣地亚哥和妻子格蕾西拉、女儿贝阿特丽丝、父亲拉斐尔和朋友罗朗多的通信以及内心独白展开。 贝阿特丽丝问妈妈格蕾西拉,“爸爸为什么坐牢?” 格蕾西拉说,“因为他懂政治。正确地说,是因为政治行为。” 女儿没有追问,为什么政治行为就要坐牢?所以,妈妈也不用回答,那是因为军政府上台了。 年6月26日,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军方成立独裁政府,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工会领袖和异议人士。在军方看来,作家圣地亚哥就是异议人士。据当时报道,当时乌拉圭全国总人口约为万,超过60万被监禁,30万流亡海外,许许多多的人被秘密杀害或失踪。曾经的“南美瑞士”瞬间变成大型监狱,恐怖令国民噤若寒蝉。 在课堂上,有学生问拉斐尔教授:为什么您的国家会从一个稳定的自由民主国迅速变成一个军事独裁国?拉斐尔只是含混地作了解答,在黑板上写下了诸如“时期”、“特征”等词汇。 至今,这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对历史来说时间不长,但是对一个人来说是人生的大部。我觉得必须先弄明白这个“为什么”以后,看清了圣地亚哥的天空后,才算真正读懂了这本书。 二 除了足球和球星苏亚雷斯,我对乌拉圭了解并不多。 度娘说,乌拉圭位于南美洲的东南部,北邻巴西,西接阿根廷,东南濒大西洋。属温带气候,资源丰富,自然风光优美。国土面积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贵州省。年人口万,比湖州人多,比嘉兴人又少。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乌拉圭是印第安人的家园。年,西班牙人来到了这里。年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你争我夺。年,西班牙殖民者建立蒙得维的亚,乌拉圭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年,短暂并入巴西后宣布独立。乌拉圭人大多信奉天主教,历史上虽然不乏党争与独裁,但与邻国相比总体而言还是相当的稳定繁荣,有“南美瑞士”的美誉。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资源的开发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乌拉圭和南美其它国家一样,经济开始增长,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南美远离战场,又出口大量军需物资,经济更是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然而,充分自由发展的经济,如果缺乏政府的二次分配以及资本的宗教善意,势必形成垄断,堕入陷阱。乌拉圭也是如此。二次大战后,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以资本财团和教会组成经济寡头,垄断了大部分经济资源,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社会失衡,政府对军队的倚重也越来越盛。 欧洲经济复苏后,乌拉圭以及南美的出口急剧下降,乌拉圭经济出现停滞,通胀增加。经济危机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导致社会动荡。而此时古巴革命的成功,乌拉圭也出现了左翼党派,它们引入社会(马列)主义,动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开展罢工、游行,甚至模仿格瓦拉,进行城市游击战,试图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来解决国内危机。 面对社会主义左翼狂潮,强势的军方认为文人政府已无法应对社会危机,便从“宪法独裁”一步步走向“军事独裁”,用残酷的手段镇压反对力量。圣地亚哥这样温和的异议人士也遭受多年的监禁,身心、家庭俱损,甚至连季节都不再完整。 读到这里,我突然有点不怀好意地想,如果圣地亚哥的左翼革命成功了,危机真的能够解决吗?未必。道理不多讲了,直接看结果,比如左倾如阿根廷庇隆,比如极左如古巴卡斯特罗。阿根廷庇隆、古巴卡斯特罗跟军事独裁一样,对人对经济也造成极大的伤害。从这点上来看,圣地亚哥们受的苦,也许就是一种宿命。好莱坞竭力推崇《比隆夫人》,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唱得涕泪俱下,但我还是对夫人的执政方式保留了一丝警惕,同样对于曼德拉,我敬佩监狱里的他,有硬骨头,而非作为南非总统的他,因为治国不能光凭硬骨头。 左翼,讲究公平正义,政策表现是加税,重福利,是好事情;右翼,讲究自由与竞争,政策表现减税,增加企业活力,亦不是坏事情。实际上,他们的口号都非常具有诱惑力。但真理过头了半步即为谬误一样,左右摆过了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都是灾难性的,都将给社会造成万劫不复的后果。 但是,左右不过头的“定海神针”在哪里?如何造就一个不受狂热宣传和极端宗教操控的社会? 三 年,乌拉圭出现了转机。军人政府决定逐步还政于民,政治犯陆续得到释放。入狱五年的圣地亚哥也在忐忑中等待出狱。 五年岁月敲打,等待他的春天还是完整的吗? 书读到这里,我已经知道,他的春天已如破镜一般缺了一个角。 在狱中,圣地亚哥给父亲拉斐尔的密信(监狱里居然还能够写密信)中提到,他在逃跑拘捕时掐死了一个协警,这个协警居然是他的表弟。这让他痛苦万分。他获得了父亲的理解和劝慰。 圣地亚哥不知道的、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他妻子格蕾西拉已经不爱他了,更要命的是居然爱上了他的好友罗朗多,并经常同罗朗多上床。 这让格蕾西拉非常困惑。她的三观和政治信仰与圣地亚哥完全相同,但是每次接到丈夫寄自监狱的信件时,仿佛是一个和她不相干的人写给她似的。身体、情感与信仰在她身上出现了割裂。为此格蕾西拉深感痛苦,不知道该不该写信告诉狱中的圣地亚哥。 格蕾西拉把这种困惑和痛苦向公公拉斐尔作了倾诉。 读到这里,也许我对南美人那种诚挚地追求自我身心的统一、不违背身体和情感的真实感觉不可理解。但不正是这种诚挚地追求真实的生命状态造就了他们享受迎面而来的春天,即便这个春天是破了角的。 那么,拉斐尔会有什么反应呢?当他当面听格蕾西拉说,作为女人已经不爱圣地亚哥,不想再和他上床,而且,而且她爱上了圣地亚哥的朋友罗朗多。 拉斐尔说,也许这会有点悲哀。假如圣地亚哥没在坐牢,这件事并没那么严重。我相信我儿子最终也一定会理解我。但是他现在在监狱里。 当格蕾西拉向拉斐尔讨要建议时,拉斐尔说我的主张是等他出狱后再告诉他,你得继续伪装。我知道这会让你不好受,但你是自由的。等到他出狱后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他,可以面对他的痛苦。你可以告诉他,是我让你对他隐瞒的。 此时,他们都能预想并体验到圣地亚哥的痛苦甚至崩溃,他们也为此而痛苦。因为儿子,拉斐尔甚至感到自己比儿媳更紧张,他害怕她会哭起来。格蕾西拉也感觉到了,她伸出空酒杯,故作轻松地对拉斐尔说,“给我再倒点吧。”拉斐尔的宽容让格蕾西拉觉得不该让这位老人那么紧张。 其实,更为焦虑的是获释后的圣地亚哥。在飞机上,他神情恍惚地想象,格蕾西拉、贝阿特丽丝以及拉斐尔、罗朗多会不会到机场来迎接他?此时,已经出狱的他并没有足够的信心来迎接他的重获自由。圣地亚哥表现出来的疏远感和格蕾西拉的淡漠感是不是同出一辙?而我分明从中读出了他们内中表露的还是替他人着想的细腻、宽容与感同身受。 当圣地亚哥走出机场,还是遇见了前来迎接的妻女、父亲和好友。 书中结尾处,作者用圣地亚哥的口吻诗意地写道:他们的确在那儿,是他们,确实是他们。去他妈的,我真高兴! 春天向圣地亚哥迎面扑来,破角的尖刻锐利,藏在故事的背后,会将这位历经磨难的不屈者刺伤吗? 掩书叹息。 尽管劫后余生的他们,生活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轨道,但是他们依旧保留了教养、宽容、慈悲和温情。革命者的信念和行动,并没有消解这些品格和情感。这是让真实生活展开的力量。也正是这种力量,而非矫枉过正的革命行动,在矫正现实社会的左右失偏、生活失常、人性失态…… 想起诗人王家新的赠言“天空完整,花朵开放”,就此打住。 年3月28日 于莫干山见山庐 莫干山读书会 编辑|麦子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diyagea.com/sdygdx/7951.html
- 上一篇文章: 许艳到底多艳,能让这么多人ldquo
- 下一篇文章: 如何改善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