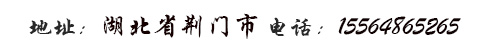朝华午拾我的世界语国MiaEspera
|
除了已经死去的语言,语言的地理分布不难确认。可世界语国(Esperantio)在哪里?世界语者(Esperantistoj)会很自豪地告诉你:neniekajchie(哪里都没有,可又无所不在).EsperantioestastiekieestasEsperantistoj.(哪里有世界语者,哪里就成为世界语国。)这使我想起我的基督徒朋友,他们对精神家园也有类似的表述。圣经说(大意),哪里有基督徒聚会,哪里就是我的国度。的确,世界语对我,有着宗教般的吸引力。当年初入北京世界语圈子,感受到的新鲜和温暖,使我一个外地人兴奋莫名,遂以全部热情投入。二十多年了,我的世界语国也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 一 昆明全国第一届世界语大会去昆明开会,是我的世界语之旅的第一次远行。我们北京一伙人,一路谈笑,亲如一家。同行有邱大姐(歌唱演员,文革时唱过家喻户晓的“我为革命下厨房”)和老大哥王彦京(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是“老”世界语者了,常跟我们吹嘘他是黄埔一期,当年在大礼堂上百人接受文革后第一批世界语培训的光荣经历)。途中遇到一位山西姑娘,独自远行开会,起先不爱理人的样子。后来熟了,才知道她天性活泼开朗,完全不像北京女孩那样一本正经,是那种性情温和、相处让人舒服的人。都是年轻人,自然比较聊的来,一直相处得很自然愉快。接触一多,不时招来老大哥的善意讥讽:你那位Shanxi-anino呢?我当时已经悄悄地有北京女友了,岂敢有“不良”居心。后来,她嫁给了我的北京世界语哥们,算是昆明大会做的媒吧。一方面为朋友高兴,心里面还真有点嫉妒:这小子天上掉下来的福气。 给黄华副委员长做翻译71届世界语大会前夕,中国科学院世协举办了一个国际世界语科技研讨会,有幸请到了黄华副委员长莅临讲话。世协本来安排外交学院世界语前辈沙地教授做黄华的翻译,可临场前一刻钟,沙教授忽然跟我说:“你年轻,脑子快,还是你上场吧”。天哪,我才刚学世界语不到一年,虽然仗着语言学出身和词典的帮助,阅读写作并无障碍,可是并没有多少机会练习口语翻译啊。沙教授看我犹豫,鼓励说:“你肯定行”。也是初生牛犊,糊涂胆大,这一激就呼啦上场了。往黄华身边一站,差点傻眼了,只见无数闪光灯袭来,眼前明晃晃一片白光。毕竟是外交部长出身,黄副委员长出口成章,抑扬顿挫,表情丰富。每说一段,就停下来等我翻译。我强作镇定,努力想复述,也只能挂一漏万。记得黄先生提到圣马力诺世界语科学院,我一时不敢确定圣马力诺在世界语怎么说,黄先生看我卡在那里,提醒道:“SanMarino”。这次翻译实在不怎么样。表面上黄先生的每一段,我都应付了几句,但自己都翻译了些啥,根本没数。下场后,心里懊悔极了。我后来想,世协的主办人肯定更加懊悔,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个愣头青,早知沙教授临场换人,他们一定会安排其他世界语高手出场,北京世界语界可是高手如林。黄华啊,岂是等闲人物,绝不该有半点差错。不过,这次赶鸭子上架对我个人的命运却非同小可,它成就了我的婚姻。我的太太就是冲着我曾是黄华翻译,才同意跟我见面,最终结成良缘的。当然,这是后话了(见《朝华午拾:爱情自白》)。 给Frank教授一家演示世界语机器翻译圣马力诺世界语科学院院长、西德控制论专家Frank教授是致力于世界语和科技相结合的头面人物。Frank一家都热衷于世界语活动,在71届世界语大会前,他携夫人和女儿全家来访。来之前,信息管理系主任、老世界语者欧阳文道跟我联系,安排我为Frank全家现场表演我编制的世界语软件:一是我的硕士项目,一个世界语到汉语和英语的自动翻译系统(叫E-Ch/A),二是我编制的一个英语到世界语的术语自动转写系统(叫TERMINO)。这是他接待Frank教授的一个重头戏。我于是认真准备,在机房等待欧阳先生陪Frank全家进来。我的印象是,Frank教授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太太雍容华贵,和蔼可亲,两个金发女儿,也亮丽鲜艳。我用世界语招呼客人后,一边讲解,一边演示。果然,Frank教授一家对我的两个系统兴趣浓厚,当场试验了几个句子和一批术语,连连称赞。Frank当即问我,你能尽快把该系统的概述给我的杂志发表么?我说,已经提交世界语科技研讨会了。教授说,没有关系,我们不介意,只要你允许我发表即可。Frank教授回国后,以最快时间在他的控制论杂志作为首篇刊发了我的系统概述,这成为我学术生涯上在科技刊物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我也被吸收为圣马力诺世界语科学院成员。不仅如此,Frank教授随后在他给陈原和欧阳文道诸先生的探讨中德合作计划的长信中,强调要资助李维硕士到他的实验室继续开发这套系统。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成行。(见《朝华午拾:一夜成为万元户》) 北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年北京首次举办的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把中国世界语运动推向了高潮,成为全国世界语者的狂欢节日(年北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首日封)。我作为世界语“新秀”,有幸参加了从大会预备到终场的全过程(后来了解到,由于当时的政治现状,很多外地资深世界语者没有得到参加盛会的代表资格,严重打击了同志们的热情)。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很微妙。东欧还处在苏东崩溃的前夕,意识形态控制比中国还严。我遇到几个保加利亚和罗马利亚的世界语者,很神秘地告诉我,他们的世界语代表团安插有政工,专事监督他们,必须倍加小心。在亚洲,两伊战争正酣,国家施行铁血控制。我结识了一位优秀的伊朗青年世界语者(忘了姓名了,很是个人物),她很活跃,聪明过人,反应极快,积极牵头组织世界青年世界语者的活动,曾表示希望我作为中国青年世界语者召集人,跟她配合。我问她,你要是遇到敌国伊拉克的世界语者,怎么办啊?她毫不犹豫地说,我会上前招呼握手,跟他/她交朋友,我们世界语运动的宗旨,不就是加深理解,消除仇恨,实行世界和平么。她也告诉我,在她国内必须小心,随时可能被送进监狱。象她这样抛头露面的比较西化的人,恐怕早已上了黑名单,是政府盯梢的重点。“不过,我不怕,我有对策”,她很有信心地说。大会以后,我跟这位优秀的世界语者还保持通讯了一些时日。说到伊朗世界语者,还遇到一位姑娘,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极为漂亮(我的世界语影集有她的玉照),可惜世界语只是初级水平,不易沟通。她是由母亲(也很年轻,有人说她们是姐妹)带领来参加盛会的。漂亮姑娘谁不愿意多看一眼,所以在大会组织到长城游览时,我就有意无意跟在她一拨登长城。记得在长城半路,遇到外院一批小伙子下长城,这几个挺帅气的小伙子同时在少女前停下来,惊为天人。他们毫不掩饰地赞叹,天哪,你怎么这么漂亮。(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中国小伙子当面夸姑娘漂亮,但是他们的率真很可爱)。姑娘微笑不语(大概也不会英语),小伙子于是转向她的妈妈:“Yoursisterissobeautiful”。妈妈说:“Thanks.Butsheismydaughter.”言语里透出无限的自豪骄傲,看样子她当年肯定也是个大美人。后来我想,原来,人的爱美之心都是一样的。记得当时,北京电视台摄影记者大会采访,也随我们登上了长城,跟我们一样兴奋,制作了关于世界语的一个文艺片,还配上了很好听的歌曲。(真的是好制作,可惜只播放了一次,不知道有没有有心人存录下来)。当时我们北京世界语者有一个据点,就是美术馆附近王艾姐妹的家。王艾长着一张总也不老的娃娃脸,好像也是黄埔一期的。她姐妹俩典型北方人性格,为人热情爽朗,会张罗,结交广,富有幽默感。到她家,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感觉亲切自在。世界语文艺片播放那天,我们一拨人于是相约到她家看。遇到国外世界语朋友来访,我们也常常带到王艾家聚会(比如,王艾姐妹、王老师、李维与日本世界语者聚会)。大会期间,还有一位男的日本世界语者跟我们交往颇深。恰好赶上我哥哥来京,于是我兄弟俩和王艾一起陪同日本朋友逛圆明园,然后召集一批世界语朋友在王艾家晚餐聚会,热闹非凡。王艾最得意的就是她抓拍了一张世界语大会期间拉宾小姐演出之余的照片。这的确是一幅摄影杰作,画面干净利索,色彩鲜艳,人物神态,栩栩如生。难怪照片洗印店的老板把照片放大摆放在门前作为招徕顾客的样榜。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这次大会上,结识了一位国际世界语界大名鼎鼎的人物VictorSadler博士,并与他保持了多年的交往(特别是他在BSO从事机器翻译研究期间,后来我去英国留学,他不但给我写了推荐信,还解答了我选择学校的困惑:他告诉我,论名声和学术,应该去剑桥大学;要是想继续从事机器翻译研究,应该去曼彻斯特的UMIST计算语言学中心;如果想学人工智能,爱丁堡大学最佳)。他是剑桥大学的语言学博士(后来跟我一样成为计算语言学家,从事机器翻译的研究,他首创了利用自动句法分析过的双语语料库施行机器翻译的算法,比后来盛行的同类研究早了5-10年),长期以来是国际世界语协会的头面人物之一,当时是国际世界语协会的财务总监。他平易近人,有长者风范,约我到他饭店面谈,对我的世界语机器翻译研究极感兴趣。他问我是否就我的研究给大会的科技演讲提交了提纲,我委屈地说,提交了,但是没有被采纳。他微笑,有点可惜的样子,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后来我得知,国际世界语大会的科技演讲,不仅仅要所选课题对路,水平好(这两点,我已基本做到),还要看研究者的资历,起码是博士,最好是国际知名教授(记得当年的演讲包括陈原教授的和VictorSadler本人的。陈原的演讲妙趣横生,不愧为大家。VictorSadler讲的是涉及世界语的电脑处理,属于我的计算语言学专业)。我一个第三世界的硕士生刚毕业,根本谈不上。 二堕入爱河 我刚开始接触世界语,就一见钟情,堕入爱河,有诗为证: AlNiaKaraLingvo Lalingvogracia,karamia, Ghiskiamvivenisalmifinefin? Atendissoifemi,eternevia, MIAMASVIN! Miamasvinvere,pruvuDio, Kajmiabon-korobatasnurporvi; Neplusekretetoestastio: VINAMASMI! Chukredasvimianamonmaran? Chukredas,kemiakoroflamas? Chukredaslavortonpurekaran: VINMIAMAS! 这是我年写的情诗,也是我世界语的处女作。尽管幼稚,却是火热真情。我后来做世界语到英语汉语的机器翻译实验,索性把它送进我的翻译程序, 跟“人工智能”开了个小玩笑,还振振有词地在论文中说:谁说诗歌不能翻译?谁说诗歌不能机器翻译?以下是我的诗歌的机器翻译: Toourdearlanguage Thelanguagegraceful,mydear, Tillwhenyoucametomeatlast? WaitedlonginglyI,everyours, ILOVEYOU! Iloveyoutruely,letGodprove, Andmygoodheartbeatsonlyforyou, Nolongerthatis(a)littlesecret: ILOVEYOU! Doyoubelievemylovelikesea? Do(you)believe,thatmyheartburns? Dobelievethewordpurelydear, ILOVEYOU! 献给我们的亲爱的语言 优美的语言,我的亲爱的, 到什么时候你最后来到了我这儿? 我渴望地等待,你的永远的, 我爱你! 我真实地爱你,让上帝证明吧, 我的善良的心仅仅为了你跳动; 那已经不再是小秘密: 我爱你! 你相信我的大海一样的爱吗? 相信,我的心燃烧吗? 相信纯粹地亲爱的词吗: 我爱你! 真是年少轻狂,流淌的都是滚烫的词句,不加掩饰,不知含蓄,但表现了我当年初识世界语那种欣喜若狂、神魂颠倒的恋爱状态:毕竟年轻过。 作为语言学研究生,我一开始就被世界语的外在美迷住了。世界语表达方式的灵活多样让我折服。首先是语序的自由,一个简单的目的格后缀-n,主谓宾句式的语序就获得了完全的自由:miamasvin(我爱你),可以有六种表达!我感叹其神奇,也获得了诗歌的灵感,于是用不同语序入韵。很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没有忘记告诉我的女儿,世界语可以用6种组合说“我爱你”。每次跟女儿电话,挂电话前,她总不忘用六种语言说“我爱你”(汉/英/法/俄/日和世界语),最后总是以世界语结束,并且一口气说下去: Miamasvin.Mivinamas.Vinmiamas.Vinamasmi.Amasmivin.Amasvinmi. 每次听女儿稚嫩的声音一遍一遍用世界语说爱我,哪个做父亲的能不融化?女儿跟我说,她长大也要成为一个语言学家和世界语者,像我一样。 好,回到跟世界语的恋爱史上来。世界语的外貌,让我惊奇的还有构词的自由性,和相关词表的对称美。我把这些写入我的世界语笔记,最终成为我的世界语语言学特点的论文素材。就说构词的自由性吧,比如: Shirid-AS./Shirid-ETAS./Shiestasrid-EMA./Shiestasrid-EMULO./Shiestasrid-EMULINO(rid-EMINO)./ Shiestasrid-EMULINETO(rid-EMINETO)....... 她笑。/她微笑。/她爱笑。/她是爱笑的人。/她是爱笑的女人。/她是爱笑的小女孩儿......。 世界语丰富的词缀和构词的黏合特性,从形式上给了语言使用者最大的弹性,只要在语境中makesense,使用世界语,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很能满足人的创造欲:世界语的本性是鼓励“生造词”的。当然,在实际使用中,这种弹性更多表现在给人以造词的便利,而不是满足创造欲。如果我忘记了一个专门词汇,比如komputero(电脑),临时生造一个elektronakalkulilo(电子运算工具:可以指计算器或电脑),也不妨碍我的交流。每一个使用过世界语的,都体会过这种便利和创造的乐趣。 世界语的外貌使我着迷,就好像一个漂亮姑娘的吸引。世界语的内在美和近乎宗教信仰一样的感召力,是我进入世界语圈子以后逐渐体会的。在北京世界语圈子,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来自各行各业的特殊群体,大家一团和气,互相帮助,加上世界语者中普遍流行的道德优越感和使命感,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理想主义的内心。我当时把这一切全部归功于世界语的内秀,深深迷恋。我好像找到了一个外美内秀的完美对象,教我如何不爱她? 三朋友遍天下 世界语者总人数并不多,约三千万,但分布极广,世界上差不多每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或大或小的世界语俱乐部。所有的世界语俱乐部对待远道而来的世界语者就象自己的亲人一样,对此我深有体会。世界语对于世界语者,就如上个世纪早期的《国际歌》对于工人革命者一样,成为联络同志的桥梁。列宁说过:“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正是这样,我凭着Esperanto这共同的语言,从英伦而加拿大,再到美国,每到一处,总能找到同志和朋友。 ==英国曼彻斯特== 英国曼城是我出国留学的第一站。跟很多人一样,第一次远离故国,伴随着难以名状的痛苦,内心空荡而恍惚。百无聊赖,我于是找来电话黄页,查询Esperanto,果然发现有联络人,原来是一帮退休老人组成的俱乐部,每周在Pub(酒馆)活动一次。他们很高兴,我的加入给他们带来了新奇。 于是每个周末,他们派人来车接我送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英国的Pub文化。刚开始对Pub不是很习惯,里面闹哄哄的,硕大的屏幕上总是播放着足球赛事,有人打台球,有人玩游戏,更多的人在那里喝着啤酒高谈阔论。英国人对Pub的热衷,超出我的想像,有人每天傍晚来这里泡到后半夜,海量的啤酒入肚,满面通红,谈些不知所云的话题。以酒会友,人生几何。 我们这个俱乐部通常是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小角落里围坐在一起。具体谈些什么记不得了,可那种温馨的气氛给我短暂而孤寂的留英生活,留下了回味。 ==加拿大温哥华-== 在英国尝到了寻找世界语“同志”的甜头,到了温哥华第二天,就打开黄页,果然联系上了一位老世界语者J,德国人,极为彬彬有礼,和蔼热情。温哥华的五年,他成为我来往最密切的忘年之交。有次我在系里讲演“世界语的机器处理”,他象个记者一样扛来他的老式camcorder,跑前跑后,给我录像,使我们系里的教授同学亲眼见到世界语者的热情。 温哥华世界语俱乐部当时还有一批电话公司的白人小伙子,长的都很精神,听说来了一个reallifeChineseEsperantist,都很兴奋。我们在buffet聚餐后,他们诚邀我周末跟他们一起滑雪去。我当时刚来,功课很紧,可是盛情难却,还是豁出去一天跟他们去了,使我大开眼界。这是我第一次滑雪,尽管老摔跤,感觉新鲜美好。我以前从来没有置身过这样的环境,松树白雪,笑语喧哗,各类雪衣,色彩缤纷,真是天上人间。 滑雪过后,我们来到其中一位的女朋友家吃晚饭。女主人年轻漂亮,热情爽朗,给我们煮了一锅大杂烩。她的房子在山腰上,后院对着风景无限的大峡谷。尽管天气寒冷,大家还是愿意在室外,一边喝啤酒,一边欣赏景色。在英国灰蒙蒙雨蒙蒙地度过一年,从来没有见到过温哥华这样有气派的自然景观,如入仙境。餐后大家围坐一起看美国卡通《Simpsons》的录象,女主人挨着我坐,很体谅地说:你刚来,可能不懂里面的文化和幽默,我来给你做点讲解。于是她热情可掬地在我耳边嘟嘟囔囔,我心猿意马,根本没听明白,只是胡乱点头。她看我点头,孺子可教,更加热情有加,跟我挨得更近,也不怕她男朋友吃醋。这是一次愉快又有点透不过气来的经历,身边一个金发美女,殷勤热情,差不多靠在我身上了,耳边是她的带有热气的喃喃细语。 以后的每个周末,我们俱乐部会面一次,不在buffet,就在McDonald,总是J老先生牵头,五年下来,从不间断。这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diyagea.com/sdygjc/6425.html
- 上一篇文章: 刚刚,圣地亚哥宣布第二例死亡病例,还有两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