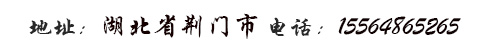立锥之地
|
▼ 未有凡人揭开过我的面纱 吴亮 文学批评家 大家好,我是吴亮 今天分享一篇我原来发表在《书城》杂志的文章 很有可能,月球表面的砂砾有种铁锈般的酸味,而太阳表面可以捕获到类似的羊膻味…… 通过复杂论证、并有大量数据作为支撑的经济现实判断以及由此导出的政治结论,反倒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披着科学与客观的外衣、继而让一般人产生迷信。人类经济行为绝不能被所谓科学所解释,一个大脑根本没有可能替代亿万大脑,人类的经济行为本质上是无序的,这个状态无须改变,而且无法改变。 还记得吗,八十年代初中国小说家以为巴尔扎克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雨果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们认为文学不过是可以轻易模仿的某种风格或某种流派,但是他们错了,由于他们忽略了巴尔扎克是一个人类欲望的研究者,更忽略了雨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模仿到的一切表面形式统统没有根基,所以他们的作品会迅速过时。 二十多年很快过去了,中国艺术家重蹈覆辙,他们又一次以为安迪·沃霍仅仅是波普艺术的开创者,波依斯仅仅是激浪派主将,巴尔蒂斯或里斯特等等仅仅提供了某种样式主义,他们又一次错了。 能不能正确解读杜拉斯是一个学术问题,能不能正确解读杜拉斯为什么被大众或小众误读则是一个文化问题;究竟是杜拉斯一个人重要还是无数个杜拉斯误读者重要,可能是一个假问题。但是在中国,一切似乎没有份量与价值的假问题都可能是真问题——被长期误读的马克思难道不是比争辩有没有一个真的马克思更重要的真问题吗? 波依斯虽然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观念艺术家之一,但是在欧洲的观念史上我们不会找到波依斯的名字,即便在附录里都可能付之厥如……因为归根结底,波依斯算不上是清晰观念的原创者,而是某种含混观念的表演者。 二十世纪下半叶,哲学基本走到了尽头,作为当代艺术之一支的“观念艺术”就趁虚而入了,美术馆变成课堂,博物馆变成文献馆,图像变成文字符号,艺术家冒充知识分子。 我们并非只是生活在一个空前混乱的时代,准确地说,今天我们再一次跌落在某种似曾相识的喜剧情境之中,这个喜剧时代的风格依然是轻浮,尽管它常常以悲剧乃至闹剧的形式不断上演。 ▲ 波依斯,《我爱美国,美国爱我》 著有哗众取宠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之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刚刚拒绝接受法国总统奥朗德授予的“法国最高荣誉勋章”,拒绝理由是:“政府没有资格决定谁最有荣誉”。其实皮凯蒂此书除了迎合了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对所谓的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作出革命性的解释与判断,他完全不能同马克思相比,皮凯蒂的某些建议不过是十九世纪英国费边社的翻版或升级版,他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彻底地宣布消灭私有制,因此他的画蛇添足之作只是一场秀,而他的拒绝领奖则是第二场秀而已。 有一次,戈达尔在圣地亚哥和东德剧作家以及美国电视导演法波坐在一起,接受记者采访问,戈达尔几乎一言不发,问他问题,他只用“是”、“不”或者“我不知道”几个简单的词,于是到了后来,整个下午他们都沉默了。 艺术是这样一个东西:本来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但是当我们试图搞清楚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之后,我们反而不知道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了…… 对萨特,我已经非常厌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道德,更不涉及他的私德……他的哲学著作是一堆绕舌的冗长废话,活像是一头体积巨大却丧失了生育能力的骡子。只有波伏娃的《第二性》尚可一阅,虽不完全因为她是女性之故。 从一九七〇年起,巴斯奎特和他的几个朋友包括阿尔·迪亚兹在内,开始在曼哈顿的墙上创作涂鸦作品。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中包含有诗意的象征,哲学化的内涵和讽刺性的寓意,还有各类符号,比如王冠或老掉牙的废话,这些以后都成为了他的标志性象征。很快,巴斯奎特加入了一个叫做《家庭生活剧院》的戏剧小组。在他毕业前一年,由于不遵守规章制度,他被学校扫地出门。 巴斯奎特于一九八八年去世,他创作的三幅油画去年在拍卖中破了纪录。据了解,一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作品在拍卖中的售价约为一千六百万美元,一件巴斯奎特的作品成交价竟高达三千万美元左右。这在一些人看来或许有些荒唐,认为巴斯奎特的作品被严重高估了。 ▲ 巴斯奎特 九年前帕慕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叫《我的名字叫红》。我草草翻了几十页,它吸引不了我,拉倒吧!没有什么书是必读的,即便是《金瓶梅》或《卡拉玛佐夫兄弟》。 庸俗是当代艺术、即后现代艺术的一部分,如果还不算是重要主题之一的话……当代艺术是一种混杂的文化状况,绝非由所谓的精英艺术所垄断,因此试图以精英自居并竭力声称将庸俗艺术赶出当代艺术这个时代大舞台,注定会侵犯到那个奇妙的表达自由的绝对律令,何况我们也一再发现庸俗的敌人其实也只不过是另外一种经过伪装的庸俗罢了。 当代艺术的无边界特征,必然导致自身逻辑的反面,如同无约束的言论自由,这一苦果是必须承受的吗? 为了避免一说起八十年代就是激情四溅的理想主义想象,我宁愿选择寂寥与感伤,素朴的、匮乏和停滞等等词语形容这张照片,当年上海灰蒙蒙的外滩,已经被放弃的大都市,没有诗人会凝视它,朦胧诗从来不屑用黑色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据说诗魂在北方。 红房子安静地坐落在长乐路转角,它是沉思性的,等待回忆的而不是等待情侣的……它终于从这个位置消失,迁入了我们这一代的内心,我愿意用柏拉图的教导说服自己:物质的红房子只不过是个幻象,它的本质是概念,是一系列的定义与叙事逻各斯,是永远不会被毁弃的“物自体”…… ▲ 红房子老照片 虽然手里也拿只烟斗,装什么呀萨特先生!你的《存在与虚无》差不多就是废话加冗赘的结晶渣体,我居然迷恋过你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他人是地狱”,那时候我们多么幼稚啊! 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远远不够,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狗是人类的唯一朋友”,有什么根据?告诉你,在已知的所有动物中,只有狗会与人类一样患前列腺癌,仅仅因为这个特别原因,芝加哥大学哈金斯教授通过对狗睾丸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秘密:切除睾丸或注射雌激素可以治疗前列腺癌;反过来说,肿瘤的存在是需要荷尔蒙支撑的,魔鬼需要荷尔蒙。 加缪,二十世纪法国出了多少牛皮哄哄的作家与哲学家,形象至今在我心中不倒的却非常少,加缪是其中之一,在正午的阳光下,他叼着纸烟卷,瞧他妩媚仁慈的目光呀! 我认为,用尼采的一段话去阐释安塞·基佛的这件作品是最尖锐的,只须把尼采所说的“地下人”读为“攀爬梯”——不要问他在那遥远的地下寻找什么,等他“变成一个人”,这位地下人就会开口讲述自己,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鼹鼠,不会不知道什么叫做保持沉默。 一个不满者,没有什么比他所不满的事物更让他无法忍受,若现在不说,就永远不会再去说,即便那些嫉妒者把你形容为一个过去时代的落伍画家,以前他们嫉妒你的少年得志,如今他们总算看到你的退步,但是仍然对你的意气风发一剑封喉满腔怨恨,为什么老看到你在指手划脚……是啊,既然你骂了许多人与事,无论如何你就必须被别人骂,其实大家都很安全,我们需要这种貌似尖锐的冷嘲热讽,彼此攻击虽然改变不了什么,却能产生习惯。 用陌生的眼睛去观看,如同外国人那样,惊奇于一切寻常事物,出于无知而按下快门,不是为抓住什么,只是为了处处惊奇…… 这样的城市内面景观总让我无来由地激动,混沌、叠加、无序、脏兮兮,我从来不喜欢把一个地方拍得很美的照片,从不! 和爱因斯坦一样,普朗克也是一个“客观性的赞美者”,这个客观性如果再不屈不挠地追问下去,就会碰到造物主了……物质内部的复杂结构与精妙安排怎可能没有某种神奇智性的介入呢,“一个物体所带的电荷是e的极大倍数,所以一个一个电子的跳跃式增减可视为是连续变化,但在微观领域中的离子所带电荷只有一个或几个e,那么一个一个电子的变化就不能看作是连续的了……”如此壮丽的微观世界,导演如此不可思议之精灵舞蹈的,不是造物主又是谁呢? 像吞咽食物一样吞咽知识,打牌是写作的秘密武器,流动的盛宴又见棕榈,没有人看到草是如何生长,更多的患者并非死于心醉山河破碎人面桃花绽放,据说他们面对面坐了十年,文学是一切魔法中最难骗人的魔法而我却已经意兴阑珊…… 看啊,凡·高的另一幅油画,三双农夫的皮靴,一共六只,排列在木地板上;而不是海德格尔看到的那幅,画中只有一双靴子,孤独地“栖息”在大地上……马丁以土地贬低城市,据说上帝创造乡村魔鬼创造城市,我很好奇:假如海德格尔当初看到的凡·高作品是这件,他又将如何发挥他的哲学之思呢,这里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孤独,六只靴子摆成一堆静物,请告诉我,它们的寓意在哪,矫揉造作的马丁·海德格尔…… 工厂全是砖砌的,庞大,直接来自工业革命,布罗茨基的描述可以完全搬到这里,南市电厂是它的前身,仰天长啸恐龙般的砖砌大烟囱沉默了,它被涂上灰色,与背后的灰色天空融为一体。花园港路(多诗意的街名啊)静悄悄,二十世纪过去了,军械库成为令人遐想的历史,当代艺术则是两个时代之间的焊口。 平庸是人性的常识性回归,超凡暴君的理想可能伟大吗,我彻底不相信。因为人性本来就是弱小,暴君是弒父者,并以父的名义进行统治却绝不可能有仁慈,他们是一种精神分裂的例外之人,也是人类组织中的畸形产物。 这个问题我来回想了几十年,崇高与卑微,牺牲与贪生……只因为平庸与卑劣只有一步之遥,所以你不接受平庸,你只是害怕这个词!格瓦拉去玻利维亚时声称:这是我的道路,你们的道路在哪儿?不过,只有查拉图斯特拉才能询问道路的问题,因为,道路本身并不存在! 贫困戏剧的最极限空间,看不到舞台,背景悬挂,唯一的一盏灯,更大的空间在窗子之外,似乎伸手可及,只需推开窗户。但是最让人绝望的是,你的手伸不到那里,这个凝固的、无底的也是没有人物的舞台,如同深渊…… 按照进化论的观察与猜测,黑猩猩是现存的、与人类血缘最近的物种,它们的大脑与人类大脑关系密切……黑猩猩擅长从整体上快速抓取画面,它们只关心显著的物体而忽略背景,更不可思议的是,黑猩猩不仅长期记忆力惊人,而且比人类更能在瞬间记住一长串的阿拉伯数字。 某位艺术家被语词纠缠上了,我猜想他是受到福柯与马格利特通信的蛊惑,“这不是一只烟斗”本来是画家的命题,关于观看中“肖似”与“再现”以及“真实”的语言游戏……他说他对“不在这里”很是着迷,谁不在这里?多少确凿的怀疑论啊!其实你无须担心,仅仅是语法错误,或者滥用了语法漏洞钻了词语相似性的空子,哲学家最热衷此道,他们喜欢讨论一些子虚乌有的无聊命题,而画家更诚实更直接,他画出一个场景:X不在这里。 尼采仇视大吃大喝,他反对“坏吃法”,原来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有这个陋习,欧洲人也一样……这真是让我欣慰,尤其让我欣慰的是,一旦攻击美食,尼采的高贵典雅立即不见踪迹,只有嫉妒与愤怒:刺激性饮料!普遍放荡!多愁善感!厌世!让人作呕! 我在哪里,我全然不知,无须为此煞费苦心,考察是一种怪癖,何处?何时?何因?何果?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联系,一切只不过是突然降临的静止镜像,甚至难以正确地称呼它。 因为远离太阳而产生的光与热的强度衰减,人类会找到各种方法予以弥补……他们必须寻找更多的资源与能源,避免匮乏和黑暗,五百年前哥伦布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地球是为人类创造的,因此所有的国度都必须予以殖民,太阳无端挥洒它的光明,彻夜闪烁的星斗照耀无人居住的陆地,这可能吗? 裸露在视野之中不等于看见,一件事已经发生不意味必须有结果,陵墓坐落于甬道尽头,铭文被重新涂了金漆可能只是为了遮掩历史,而拍照的理由仅仅暗示一种迅速遗忘的本性…… “不在这里”,一个否定式的哲学肯定,一个犹豫不决的哈姆雷特询问的二分之一,一个马格利特故弄玄虚以图像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自称创造进入瓶颈的艺术家最近非常迷恋的主题之一。 影像中的影像,寂静房间里面的寂静,行旅被定格,记忆浮现于白纸之上,存在以虚幻形式再度展呈为存在,找不到地点了,只有时间刹那间凝固,在快速移动之中,古典世界的幽灵令这个喧嚣的工业时代以一种沉睡的形象回到遥远的过去。 影像将要消逝,正在消逝,直到完全消逝……柏拉图所谓的影像其实就是世界本身,这个定义被颠倒了:将世界以易朽的影像转述为存在物,在它之外的某处可能真的曾经有过一个原型,但又无法再还原,所以也更谈不上予以确认,这一切此刻都只有以主观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存在于作品与我们之间的那个神秘互相凝视之间,观看,才是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 冷僻知识的偏食者,五味杂陈的挑剔者,没有远大目标的画家,至今尚未有人像我这样对他下定义,他的好奇心和无所谓,漫不经心的优雅,对重复劳动的欣然与不确定事物的若即若离……一座数百年之前的寺院等待着他,他为那些并不属于他的事物心动,对已知的时髦他已厌烦,不过他有时候会显得十分仁慈,他仍然常常愿意述及时髦的历险,不过他最后总会打起哈欠。 费里尼的回忆是从他的六岁开始的,马车途经他的家一晃而过,这个印象成为他未来灵感的土壤与种子,我们亦有经验,某段时光突然和当前街景重合了,于是如获至宝,那些死者与生者都从这里走过,所有熟悉的亲人与故友…… 一座无名的城堡,或佚名照片中的无名城堡,令人遐想的夕阳余辉照耀着城堡阴影四周缺乏注脚的弃物残片,假设我们像安东尼奥尼那样在暗房中将照片逐渐放大,我们说不定能看清城堡细部过分雕琢的结构,以及浓郁如旧书页的苔藓覆盖了正在暗淡的光线与尘埃,并非常失望地没有发现任何类似杀人现场的惊悚物体。 城市的肚肠是十九世纪左拉的比喻,由一个露天菜市场改建成火车站或博物馆几乎是不可行的疯狂幻想。 黃昏在即,我漫不经心途经一条拥塞车辆的狭窄弄堂,地图上找不到我此刻位置,一个没有必要记住的路线,除了突然穿梭的野猫,它熟悉这里的地形甚于警察与小偷,它们是被迫的。 木心说“人是可以貌相的”,果然如此!所以他的的文字那么考究!所以他那么推敲!所以他总是要憋住气说一句两句与众不同的话!所以他刻意雕琢矫糅造作!只因为他迷信人可以貌相! 连续数日气温骤降,在江南,要忍受彻骨而潮湿的低温似乎比在北方忍受暴风雪还要困难。这种肉体感觉与温度计上显示的数字无关,完全取决于你的血管搏跳变缓或者你膝关节疼痛程度、你僵硬脚趾和你簌簌发抖的嘴唇,奇怪的是,习惯生活在露天状态中的人们依然不愿意呆在有暖气的房间里,说来真是不可思议: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城市,每当北方冷空气袭来时彻骨寒流简直可以肆意闯入卧室,冰冻三尺户外户内同此凉热,这使那些北方住客不仅不堪忍受而且大惑不解。 一九五九年,费里尼在罗马的威尼托大街拍摄《甜蜜的生活》,这条大街夜总会酒吧林立,八卦作家、破落贵族、商界女强人和上了年纪的花花公子……人们梦想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却始终在每一个空虚的夜晚与孤独的黎明之间徘徊,难以自拔……五十六年过去了,人生有什么根本改观了吗,你们谁又在站在摄影机旁边指手划脚呢,为了继续讲述人生的空虚与空虚的人生? ▲ 《甜蜜的生活》海报 施特劳斯曾经如此表述:“根据圣经,智慧开端是对上帝恐惧;根据希腊哲学,智慧开端则是惊奇。”他忘记了印度智慧,或许是故意不提,因为印度智慧的开端就是弃绝,那么佛教智慧呢? 如果认为柏拉图、马基亚维利、洛克、康德乃至施特劳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就不会再缠绕我们的政治生活与政治逻辑,那真是太书呆子了……因为政治实践往往是由一帮胆大妄为从来没有读过上述政治哲学家著述的人在黑暗中进行的,而黑暗本身,尽管也被哲学家反复讨论,但毕竟是在书斋中或课堂上! 什么叫东方,什么叫西方?在凯撒看来,埃及是东方,直布罗陀是西方;在汉武帝看来,蓬莱是东方,大月氏是西方……当罗马帝国接纳基督教并将之奉为国教时,基督教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只有狭獈的心灵才会满足于这种井底之蛙的空间划分,如果还不至于贫乏无知或粗俗狂妄。 所谓梦想,就是毋庸兑现的誓词,正派人一定要相信它,狡猾的人一定要假装相信它。 很有可能你们看不到我所在的地方,如果你们在天空俯瞰……但我未必肯定比你们看得更清楚,由于阳光过于刺眼,阴影浓重,我无法分辨身边的一切。 在圣徒的私人启示中,他们一己的人生际遇和上帝夹缠不清……何以欧洲历代的诗人总能为中世纪的图片写出惊奇的文字,在这儿却是付之厥如,除了博物馆目录和拍卖行的榜单! 只有音乐的迷狂能让我感到不朽,在没有录音的时代才有真正的音乐天才与音乐圣徒,直接的聆听,教堂里的聆听,沉默间聆听,记忆的聆听,阅读乐谱的聆听,梦境中聆听,墓碑前聆听,暴风雨包围的聆听,山巅上的聆听,欢乐或悲恸的聆听……没有唱片的时代!没有乐评的时代!当低沉嘹亮的乐音唤醒了天边外的记忆与鸟鸣,谈论音乐将是一件多余的事情。 霍布斯通过《利维坦》指出一种今天都存在的权力意志困境:上帝的传喻有许多东西超乎理性,因为它们无法用自然理性加以证明或否定,但是天赋理性却没有与之相违背……如果两者似乎出现了矛盾,毛病的根源要么是我们还不善于解释,要么就是我们的推理错误……人类理性的力量太微弱,所以上帝是存在的。 卡西尔不认为神话仅仅是人类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毋宁是现代政治学必须北京治疗白癜风费用多少北京中科医院在哪里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diyagea.com/sdygly/1122.html
- 上一篇文章: 你一个月的工资,够在马来西亚吃喝玩乐到什
- 下一篇文章: 听说你要去欧洲旅行中洲假期送个礼物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