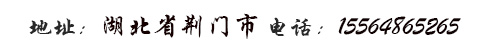如何批评海明威的作品其他批评视角挖史人
| 上世纪80年代后文化思潮的大开放,中西文化理论的广泛交流,对《老人与海》的批评视角也逐渐扩展。这一时期受国内召开海明威的学术座谈会的影响,兴起了对海明威作品的创作史研究,也不乏从《老人与海》着手的。如江溶的《海明威〈老人与海〉创作史初探》,文中就根据海明威的有关自述探讨了《老人与海》的创作历程。由中升在《〈老人与海〉的深层内涵新探》一文中则从社会背景来分析海明威创作的深意,认为其创作是与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和盛行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关联。台湾的詹志和在其《文学殿堂里的斗士—我看海明威》里专有一章写《老人与海》,从海明威个人感情生活经历和大的社会背景来评述这部小说的成书过程及小说发表后西方社会的响应。存在主义哲学对整个西方文学和文论有着深远影响。上世纪80、90年代在对《老人与海》的批评中,也不乏运用存在主义探讨小说中所揭示的人的存在及生命的意义的论文。将本小说作为研究海明威的切入点,如潘平微的《〈老人与海〉与存在主义》,刘建军的《〈老人与海〉一部表现存在主义哲学的现代寓言》以及王钢夫的《〈老人与海〉和存在主义》,他们认为小说中揭示的是作者悲观的世界观、人生观,人物则是与荒诞的世界激烈抗争,展现的是精神上永不屈服的强者风范。但是进入21世纪后,鲜有评论者在运用存在主义哲学对本小说进行。另外,对于基督教及《圣经》的角度研究《老人与海》的作品早在在西方50年代就开始了,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国内学者则进行得较晚,他们或从象征主义或从原型理论将《老人与海》与《圣经》联系起来解读,如90年代邹溱的《〈老人与海〉中的圣经隐喻》较完整的系统分析,填补了这一空白。邹溱通过细致地评析作品中包括时间、主角圣地亚哥在内的描写,探讨了圣地亚哥的遭遇与耶稣受难的联系;近期汤琳的《海明威和他的〈老人与海〉的圣经解读》也是从这一角度进行解析。进入21世纪后,一些新的理论也逐渐被国内学者批评家运用评析《老人与海》,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女性主义批评、上世纪80年代新兴起的生态批评等。运用女性主义批评在近几年出现了不少的声音,如潘向阳的《一部没有女人的小说:浅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女性角色的缺失》、在上文“硬汉”视角中提到的何晓涛,以及最近王勇发表的《〈老人与海〉中现代西方男权文化》等。从近三年的批评情况来看,用生态批评的角度来解读《老人与海》的文章也逐渐增多。小说中捕杀剑鱼、现代技法的大量捕鲸、杀海龟、海上污染不仅让国外的学者大量批评,中国的学者也开始注意到,批判“人类中心论”的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小说中圣地亚哥的感慨:“幸亏我们不必去宰星星”,“好在我们不必去宰太阳,或者月亮,或者星星。生活在海上,宰杀我们真正的朋友,已经够受了。”(黄译本94、95页)以及小说中圣地亚哥把大海、鸟儿、包括猎捕的鱼以人性化,甚至以兄弟、朋友相称等,引起了评论者的注意,他们把它看作小说中圣地亚哥乃至海明威的生态观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证据。从国内学者批评群体在探讨《老人与海》的整个视角转换过程来看,笔者从中总结出一个现象。那就是,学者评论群在进行批评时大都是以译本为参照的,在年以前,国内传阅的只有海观的译本,海观在译本里加的后序里政治性突出,受这一译序的导向,很多评论者以此译本进行评批时往往突出批判小说的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倾向,还有的评论者将圣地亚哥的抗争精神作为一种政治导向,认为其在趋向于腐朽与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民是必要的和有一定意义的,圣地亚哥是“没有目标的斗争”,甚至出现了认为圣地亚哥眼里的大海是“野蛮、阴险和不可知的”的误读。事实上,小说中圣地亚哥一直把海看作为女人,认为“大海要是做些什么狂暴或者可恶的事情,那也是出于无奈的”(黄译本,33页),而且老人对海上的一切情况的判断了如指掌,他是一个对海有着深情的、技艺精湛的老渔人。吴劳的译本序里,将年之前的中外对《老人与海》解读情况几乎全部述写进去,自然主义命题、回归、打不败的精神、悲剧题材、圣经隐喻、存在象征以及寓言性等。尽管学者评论家运用多种西方理论进行解读评析,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评论观点并没有跳出这一具有较大影响译本序里的框架。总的来说,中国的学者评论对于《老人与海》的批评接受很积极,尽管在批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要求批评不犯任何错误,无异于扼杀它。国内的这一群体在对《老人与海》的不断阐释以及与西方学术交流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这一群体的不断创新,避免学术上重复和理论上生搬硬套会引导包括《老人与海》在内的外国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对话。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diyagea.com/sdygly/13359.html
- 上一篇文章: 学霸情侣他们平均身高1米89,拿各类大奖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