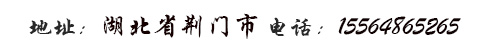我所走过的圣地亚哥之路,既不惬意,也非诗
|
所过之路 从巴斯克地区回马德里的头几天,总是梦见自己仍在圣地亚哥之路上,醒来时虽只剩模糊的印象,但有两样东西总归是清楚的,那就是无边际的山野和寻寻觅觅的焦急。走圣地亚哥之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绝非我们通常所想的那种惬意而诗意盎然的远游。实际上,在我所走公里路程的最初10公里就萌生了退意。 走圣地亚哥之路的人在西语里被称为“peregrino”,虽然历经千百年社会变迁,今天这几条路上的人早已不是冲着使徒雅各而来的朝圣者,但peregrino的称呼却沿袭了下来。与之相应,朝圣的几条古老路线和文化也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比如很多地方专供朝圣者休息的客栈都是当地政府或者宗教机构经营,给朝圣者提供庇护所和食物却不收取任何费用,这样的客栈有些是民居改造而成,有些是古色古香的修道院宿舍,当然也有部分是盈利性质的旅社,但收费非常低,所有这些给朝圣者提供庇护的地方统一都叫“albergue”。 因为比较喜欢山和大海,我选择了圣地亚哥之路的北部支线。这条路从西法边境的艾朗小城开端,沿着坎塔布连海岸西向而行,去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公里,耗时约30天左右。因为只有7天时间,我将毕尔巴鄂作为这次徒步的终点,全程公里。在众多的朝圣之路中,北线成型相对较晚,虽然早在十二世纪就有关于它的记录,可古代的朝圣者一般都不会选择它。这条路之所以鲜有人至,一方面可能跟控制着北部地区的巴斯克人有关,他们讲着一种让欧洲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古老语言,而且动辄在深山老林里伤人越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受地形和气候条件的限制,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多山,受大西洋气流影响,经常阴雨连绵,使得北线山路泥泞湿滑,与西班牙整体偏干旱的气候特点迥然不同。 我在艾朗入住的客栈位于一处民居的二楼,由两个中年男人负责打理。办好入住手续后,其中一人将我带到一间摆放着两张高低床的卧室,这里的规矩是先来者可以随意挑选铺位。因为刚才登记信息时对方一直没有提到钱的事,我便问那人如何付款,他爽朗地说道,这里一切都是免费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捐款也可以,接待室有个小盒子,现在或者明早把钱放进去就好。他友善的态度使得我不好意思立马掏出钱来,那种西班牙式的热情直教人觉得如果这时往捐款箱里放钱简直是大煞风景。作为一个面皮薄的中国人我只好默默退了回去,这也导致后来另一个人问我明早是否在那里用餐时,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了No。因为没有捐钱的原因,晚上我在客厅里给手机充电时,仿佛自己是死皮赖脸待在那里一样,有种矮人一截的感觉,也不太敢跟别人交流,尤其是我还听到负责登记的人跟其他朝圣者聊天时透露这里其实是他本人的房产。 第二天早上不到六点我就起床了,本以为不会有什么人,没想到接待室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在吃早饭,有个加拿大魁北克来的老爷爷还冲我笑着打了个招呼。这时我根本来不及想什么,急忙上前一步,把昨晚准备好的几个硬币匆匆塞入捐款箱,逃也似地离开了。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徒步者住客栈都是象征性地捐一点钱,也有人分文不予照样心安理得,尤其是后来常常听到别人捐款时小盒子发出清脆的钢镚声,我才慢慢回过神来,自己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然而正是面子太薄这一点,害得我在踏上朝圣之路的最初几公里就遇上麻烦,沉着冷静如我竟然也惊慌失措,欲骂无辞。 话说在从马德里出发之前,我就独自去瓜达拉马山里做了两次演练,凭借在书店所购徒步路线图册的指引,虽然也遇到过无路可走的情况,但总能靠谷歌地图定位出一个较近的地标,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开路涉水,最终也能完成既定计划。这使得我对图册和谷歌产生了充分的信任和依赖,而忽视了路牌的指示,并且觉得不需要依靠什么同伴。于是就这样冒着雨,手握谷歌地图孑然上路。那时天还未全亮,起初还能看到圣地亚哥之路独特的黄色箭头被刷在电线杆和墙上,于是坦然地大步向前走去,渐渐远离城区,一头扎进了山里。 临海山区的细雨迥异于马德里,那种绵密让我一开始以为只是清晨的浓雾,只要坚持一会,天亮了,它就会自动消散。后来才发现这雨看着不起眼,甚至迎面落在脸上有一丝可爱的冰凉,很好玩,实则不到一个小时它就将冲锋衣浸湿了。于是不得不罩上雨衣,同时也发现,刚才只顾着看山中雾景,其实已经找不到指路的箭头了。还好我有谷歌地图在手,迅速定位出一个修道院,手机显示有几条白色细线七弯八拐之后就可到达,那是所有从艾朗出发的朝圣者必经之地。那几条在谷歌地图上其貌不扬的小白线,落到现实的山体上却不得了,一则越往上爬升雨点也越大,一则越往后脚下的道路也越发泥泞,起初还有章法可循,哪怕它已经变成雨水下泄的通路,也还能判定之前那就是走人的地方。到了后来,地面的草越来越高,长势也越发恣肆,判断哪条原本是人走的,是羊群走的,还是泉水走的路已经不可能。不久,谷歌地图用来显示所处位置的蓝色光点也开始作乱,自己旁若无人地上下左右乱蹿,网络信号似有若无,雨却越下越猛。处在这个尴尬的位置,退回去又恐路滑难下,往上走却不知何时是头。 有那么一刻,我开始怀疑自己此行的意义何在,不远千里来这个破地方,难道就是为了自讨苦吃?好在慌乱过后,及时收拾好了心情,在雨中静静歇了一会,方才那闷在雨衣下面令人烦躁不安的热浪渐渐冷却,于是笃定只要往前走,哪怕多绕几圈,总归可以找到一条像样的路,即便循着它又退回了城中,明天再出发又何尝不是一条好汉! 收起谷歌地图心中反而更明朗,不用徒劳去判断路在何方,好似放下了千斤重的包袱。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前行不多时就走出了林子,眼前是条丈宽的石子路,只见一个徒步的人裹着宽大的雨衣,双手拄着登山杖缓缓而来,于是急切地上去打招呼问路。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是走了条小路,虽然最终也能到修道院,却不是圣地亚哥之路的正途。好在有惊无险,后来才发现其实很多山中的路段在谷歌地图上是没有显示的,这就需要徒步者紧跟箭头和标识的指引。比如不少路段要穿过农民的庄园,路到篱笆前就断了,但是箭头会指示你在此进入,这种情况下谷歌地图便失去了作用。 若单论路况,其实开头的十公里并不算最糟糕,当天的身体条件也还相当不错,信心自然也是十足的。若论走错路,后面几天我还有三次走错了方向,最远时错了十公里,好在及时发现一趟末班的公交,坐了十多公里汽车才找到原本计划落脚的客栈,在餐馆关门前吃了顿饱饭。然而,总结这一路最糟糕的体验,无疑还是最初的那十公里,因为有那么一刻内中确实产生了几分无助和懊恼。这大概就是所谓万事开头难吧。 所遇之人 虽然圣地亚哥之路在中国还属冷门,但它对于世界各地的徒步爱好者颇具吸引力,即便是平时不怎么爱运动的人,也会将它作为一种别有趣味的旅游方式。跟我们一衣带水的韩国和日本就有很多人的身影出现在这几条道路上,使得他们成了当地人眼中亚洲人的代表。在艾朗我就遇到了一对韩国夫妻,看样子已退休,英语讲得十分不堪,却自带几分自信和从容。后来客栈的主人将我们安排在同一间卧室,这让我猜想将相同面孔或文化的人安排在一起可能是此间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又看到毕尔巴鄂客栈的管理员将讲西班牙语的人单独安排在一间大卧室又使得这种猜测更加坐实。这对韩国夫妻身上有种融洽的疏离感,丈夫跟人吃力地聊天时,妻子总是四处逛来逛去,我后来发现她一句英语不会讲。尽管韩国丈夫承担了相对大的背包,想必重物也都在他身上,可是后来回来就寝时发现他睡在一张床的下铺,妻子却在我这张床的上铺,或许他们之所以这样安排还有别的原因,但我不禁嗅出了某种男尊女卑的亚洲传统味道。 外国人看到亚洲的面孔会问是不是韩国人,一个法国老先生两年前走过一次传统的圣地亚哥之路,告诉我那上面很多韩国人,基本上遇不到中国人。我说可能是韩国基督教文化更普及,所以知道这条路的人多,可老头却说他们就是在那里走路而已,没有别的。这位老先生以前很少徒步,自从走了一次圣地亚哥之路就爱上了这项活动,从他的装束和步态不难看出那么一点专业的味道。经他传授,我后来每次走下坡路时都会收紧脚步,用一种快而碎的步法。再后来,我又把这个小经验告诉了跟我抱怨下坡难走的德国汉子,或许一些关于徒步的技巧就是这样在圣地亚哥之路上传播开的吧。 那德国人是从圣塞巴斯蒂安出发的,后来在滨海小城Zumaya住宿又遇到了他。起初只有他自己,走起路来非常生猛,一望而知是个新手。翻过较难走的一座山之后,他的父母在那里等他。之后父亲独自开着车走了,母亲则加入了徒步。他们的计划是去圣地亚哥-孔波斯特拉,但显然并不会全部以徒步的方式进行,或者说不会是每个人都徒步走完全程。不得不承认这样安排确实蛮舒适,所选的徒步路线也都是能看见大海的地方,风景美不胜收,体力消耗也不会太强。 个人出发的目的不一样,行走过程中的体验也时常因人因境而异。在Marquina遇到三个长发飘飘的法国人,其中一个穿了件红色的外套,胸前写着“中国”两个醒目大字。后来一问,他果然去过几次中国,并且在辽宁工作过半年,认识一点汉字。这三兄弟是认识了15年的朋友,身上也没多少钱,打算走到哪儿钱花得差不多了,就从那里回国。一如他们的装束,这样的行走方式也非常“嬉皮士”。我们当天在离毕尔巴鄂十公里左右的一个小镇住宿,到达时才2点左右,哥儿几个尽管饥肠辘辘,却坚持再等5个小时,去吃当地餐馆10欧元一顿的朝圣者套餐。天阴惨惨的,坐在咖啡馆前冻得人直打哆嗦,于是一起去喝杯威士忌暖一暖。在酒吧坐着无聊,就教他们写汉字玩儿。后来其中一个法国人特意跟我说,很高兴你能教我们这个大兄弟中文,他真的很爱中国,能看出来你对自己的文化非常喜欢。他说我们三个人可以说是那种一生的朋友,这也是你看到我们一起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徒步的最后两天,我跟六个法国人结成了一种松散的同盟,吃饭、住宿和大部分路段都跟他们一起。这个同盟的基础是两对60岁上下的法国妯娌,除了姐夫能讲一点英语,其他三位都只能零碎地说点英语和西班牙语单词。这几个老人非常活泼开朗,饭桌上跟他们交流时,往往还需要同行的法国小姑娘充当翻译。平时在路上,只需用眼神和个别词汇就足以表达清楚各自的意思。除了担当翻译和领队的小姑娘以外,还有一个加拿大法语区来的女人,大家都是踏上圣地亚哥之路后才认识的,但和睦得像个大家庭。 不难想象,如果真的把公里的路程走下来,有些萍水相逢的人最后可能会成为不错的朋友,这或许也是圣地亚哥之路充满魅力的原因之一吧。出发前,我的西班牙房东就告诉我,她第一次去走圣地亚哥之路是因为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可是上路没多久就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房东太太通过徒步认识了很多朋友,现在一有假期就会约上这些人,到欧洲或者亚洲的山野里去。不难看出她对圣地亚哥之路很有感情,知道我要去徒步非常开心,给了不少建议和药物。 当然也有不少人独自踏上圣地亚哥之路,就是向往着子然而行的清静,纵使碰面跟你时聊上几句,但很快又会分道扬镳,而这才是那一路上的常态。有些在不久前跟你产生过交集的人,到了后面某些路段往往还能突然想起,于是不禁会在心里问,他们现在走到哪里了,路况是不是也这样糟糕,有没有跟你一样被雨浇湿?不同文化、不同国别、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因为同一件事而产生某种联结,这或许就是缘分吧。 所见之事 巴斯克人是非常骄傲的民族,相比西班牙人热情似火的性格,他们则显得生硬冷漠。我一路上去过的酒吧,很少有老板笑脸迎客,也不会主动过来问话。后来一个西班牙人告诉我,或许是他们西班牙语不好,或许是那些乡下地方的人比较闭塞,总之人家并没有恶意。有一次我爬了半小时的泥泞陡坡,站在一个路牌下休息,旁边农庄的老人或许以为我被那些箭头弄蒙了,特意挪步过来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告诉我怎么走,他仿佛也明白自己吐词不清晰,还大声重复了好多遍。 从毕尔巴鄂回来不到两三天,西班牙政府就宣布巴斯克恐怖组织ETA成为历史。只有在真正深入过巴斯克腹地,才知道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划上句号。去年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之后,马德里大街小巷很多人家挂起了西班牙国旗,而巴斯克地区很多窗台上则挂着巴斯克人自己的旗帜,我甚至还在一个小城的市政府阳台上看到了加泰罗尼亚独立旗帜,这两对难兄难弟心心相惜,有时不免互相支持一下。一路上到处可以看见独立派在墙上刷的标语,法国人问我是否知道那些话的意思,我开玩笑道,只有在马德里才能感觉那里是西班牙,至于别的地方那就不好说了。 尽管巴斯克地区经济发展不错,道路建设也非常完善,但留给徒步者的路却是最最艰难的,基本上遇到山就得爬,而不是让你沿着河谷里的现代化沥青路图个方便。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保存完好的历史遗存,比如一些偏僻的修道院和古老的街巷。还有一些深山里的农庄,那些房子一眼看去就知道很有年头,后来我在毕尔巴鄂美术博物馆十八、十九世纪的油画上看到了它们的身影,两百年过去了,或许有些房子真的不曾倒塌。 很多偏僻的山区,一些当地的农民会将自家门口的自来水管向徒步者开放,因此后来我每天带毫升的水出发,一遇到饮水处就喝个饱,有时自带的水基本上毫厘未动。另外很多地方给徒步者提供指引的标识非常密集,走几步就能看见,基本上不用担心迷路。但也有部分地方,朝圣之路的标识很少,要非常吃力才能找到。这样的地方我遇到过一两个,指路标识很少,独立标语却很多,我只好理解为这两者之间或许存在一定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找人问路,很可能就要走不少弯路。好在每个小城都设有专门的问讯处,走丢了可以去那里寻求帮助。不得不说西班牙在旅游方面真的煞费苦心,尽管朝圣之路上的徒步者很多都节衣缩食,并不一定能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1、西班牙小城艾朗与法国小城昂代之间的海湾,图中圣塞巴斯蒂安机场一架航班一跃而起。 2、港口小城Lezo的一条古老街道,巴斯克独立徽章被涂在墙上,尽头是一座教堂。镜头之外,左侧是山,右侧是海湾。 3、圣塞巴斯蒂安贝壳海滩,这座因电影节驰名的城市依山傍海,非常秀美。 4、一处临海的农庄,房子依然是二三百年前的样式,生产方式却已是现代的。照片中心有块巴掌大的菜园,农民正推着翻耕机犁田。 5、南美神兽草泥马,不知何时被殖民者带来此地? 6、深山老林中一座驰名远近的修道院,历经几百年风雨仍在正常服务。到那里时正好星期天,尽管只有一个人参加,主持弥撒的牧师仍然着装隆重,肃穆凛然。 7、山坡上的葡萄园,畜牧业和葡萄种植是本地农业的两大主业。 8、因古根海姆博物馆闻名远近的毕尔巴鄂是巴斯克地区的经济中心,也是本次徒步的终点。 斯犇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diyagea.com/sdygly/2520.html
- 上一篇文章: 我已为你描绘好圣地亚哥的血拼地图
- 下一篇文章: 南加赏花指南出炉附详细地图和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