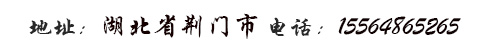逃出圣地亚哥34相遇或者重逢,无非
|
北京比较好白癜风专科 http://pf.39.net/bdfyy/ 走出圣地亚哥机场,可以看到远处那积雪皑皑的安第斯山脉。我拒绝了Leo的盛情,打算先去Sam开在圣地亚哥的公司一趟。我并不喜欢目前在管事儿的胖子小马哥,但相比起来,跟Leo一起去他未婚妻的亲戚家,会是更糟糕的一种选择。我背着我简单轻便的行李包,先后吻别了Rena和她的阿姨MariaJose,拍拍Leo的肩膀,“有事儿打电话给我。”说完我快步跑上机场大巴,先走一步。 大巴车在路上摇摇晃晃的行驶着,然后我才发现自己坐错了线路,这趟车并不经过我要去的BarrioPatronato。我跟过道对面的一位老先生询问了一下,他建议我在总统府的LaMoneda广场下车,会比较方便转车去目的地。我笑了笑,向他道谢,他耸耸肩,摊开双手说:“这有啥,小事一桩。” 我闭上眼,靠在椅背上,缓缓的回想从LaMoneda广场出发的话,该走哪一条街,没一会儿就决定放弃了,因为无论怎样,从那一带到Mapocho河边都得经过七八个街口。Mapocho河与SantaLucia山,应该算是这座城市的源头,四百多年前,Valdivia就是在SantaLucia山上举行了建城仪式,而我要去的地方,就在Mapocho河另一面的AntoniaLopezdelBello。这条河用中文译音翻译为马布乔,有不少中国人据此真把河上的一座桥称之为马步桥,还煞有介事的跟新到当地的同胞说:知道为啥叫马步桥吗?以前这桥是军队骑兵团出去操练时候必经之路,所以叫马步桥。严格说来,马布乔这个译音并不完全标准,但中文拼音里并没有完全贴切的发音,倒是云南方言说雀的读音,非常标准契合——我们云南人说到雀的时候,读音并不是que,而是qio。 “你看起来很面熟,我们应该在哪里见过面。”我睁开眼,对面的老人在看着我。 “你确定?”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呵呵,虽然我是个老人,可我的眼睛还不算太坏。”他说。“我肯定在哪里见过你。你是DonMiguel的朋友对吧?” “烟盒上的那个?”我说。“当然了,我跟他可熟了。” “不,不是,不是那个DonMiguel。”老人笑着说。“MiguelAngelParra,你认识的,对不对?”他摸了摸日渐稀疏但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我见过你,在DonMiguel家里,一次生日宴会上。” 我们聊起了共同的朋友,那个拥有一家远在新西兰的轮船修理厂以及两条大货轮的富翁MiguelAngelParra,说起来我也有三五个月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了,或许我该打个电话给他。过往我到圣地亚哥来,只要他在家,我都会到他家里去坐坐,看望一下他的太太、多年来饱受风湿病与三高折磨的Cecilia女士。 “你知道,我还从没见过DonMiguel像夸奖你一样夸奖过别人,更别说一个外国人。”老头说。“我今天要和他一起吃晚饭,你能来就太好了。” “谢谢你,不过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准确的答复。”我沉吟着,这样说话还真有点别扭,我得在心里斟酌着应答的词语,尽量让自己说得斯文点。平时我可不是这么说话的。 “如你所愿。等你决定了,就打电话给我。”老人递给我一张名片。“前面我就该下车了,祝你一切顺利。” 看了看车窗外,这一站是EstacionCentral,从这里开始往前,一直到Baquedano,间隔着七八个地铁站的区域,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地带,每次到圣地亚哥来,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这个区域里活动,成批的商品从我工作的地方被拉出来,散布在这一带的各个角落,只要我呆在圣地亚哥,每周的二、四、六三天都得在这一带转悠,看一看不同街区市场上有什么新货、把客户订的货送到他的店里、提醒那些支票快到期的客户注意不要出现跳票,以及找那些已经跳票了的客户交涉付款的问题。 在圣地亚哥做生意,和在Iquique保税区做生意,方式上是有很大不同的。保税区里基本都是美钞现金交易,连比索现金都很少有人收,更别提开期票了,但是在圣地亚哥如果你想把生意做大,不接受客户的分期支票是很不现实的,对于像我们这种完全以批发为主的公司而言,更是如此。接受客户的大量分期支票,就意味着要承担额外的更多风险。客户来自不同的商业区,实力有大有小,开出的支票五花八门,有一连开十张支票每周一张的、有开一张支票却要40天后才可兑现的、也有快到期了不停打电话给你要求你逾期兑现的……在一开始Sam就很小心地定下了一些规矩来避免过多的坏帐,比如对新客户必须是即期支票当天兑现,否则宁可不做;而对于老客户,也是根据生意往来额度的大小,规定了不同的期票数量多少、时间长短和金额大小,而且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但是随着业务的进展,加上管事人的疏忽,不到半年时间各种问题就不断地出现,最糟糕的是连账目不清不楚了。这是Sam绝对不能忍受的,在他看来,一本有赚钱却无法算出到底赚了多少钱的糊涂账,简直比一本能够清楚看出亏损在哪里的坏账更加危险可怕,所以他立即就宣布了要亲自把账目理清楚。然而兴致勃勃地干了一星期之后,Sam打电话给我,说:“你马上到圣地亚哥来,这边的账你给我搞定。”他的声音气急败坏。 老板发令,我跑的比老婆发令还要快,当然这只是个比喻。等我在圣地亚哥的办公室里坐下来,立即就明白了这事儿我他妈根本没本事搞定。我可以选择先硬着头皮弄上三五天,然后再告诉Sam我搞不定这个乱七八糟的账目,但我隐约地觉得,一旦我动手去做了,很有可能我会越来越难以启齿去向Sam坦白自己的无能为力。最好的时机还是立即说明。听了我自承无能,Sam伸出手指在空中冲我一连戳了好几下,最后说,他妈的算你还老实!这样吧你先顶着做一阵子,我同时想法找人。 我忘不了那段日子,每天晚上自己坐在办公桌前,桌子上那一堆的单据,烟灰缸里总是满满的烟头,咖啡都不知喝了多少杯。必须要说明一下的是,Antonialopezdelbello这条街最早都是独栋的住宅,后来才逐渐成为一些商人开设公司办公用,白天就没多少行人,但到了晚上,尤其是半夜,却有很多在附近酒吧区喝得半high的青年男女来回游荡,歌声、打闹声一直可以持续到凌晨3-4点;一些手贱的年轻人路过,伸手摁了门铃,直接就把昏睡在办公桌前的我像诈尸一样惊醒过来,然后麻木混沌的脑袋里全是怒火和沮丧感,完全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里。等到外面嬉笑声渐渐去远了,一股莫名的沮丧瞬间就能把你吞没,他妈的我这是在干啥!一个多月后,准确点说是39天后,Sam安排了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男子小马哥来跟我交班。把手里头所有的事情一股脑的交给小马哥以后,我立即叫上公司的三个智利小伙子,到酒吧里high到深夜。把他们都送走,我摇摇晃晃地回到Antonialopezdelbello,一路把大部分住宅大门上的门铃都摁了一遍。我记得摁到号的时候,听到里面有恼怒的声音在骂,我感觉很快乐。 如同我说过的那样,我很不喜欢小马哥这个死胖子,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我们之间就没有愉快过。这会儿他已经是第二次重返Sam的公司做事了。在我与他交接了工作之后,他独自作为圣地亚哥公司的管理者,做了七个月以后突然就不干了,买个机票就跑去了悉尼,到了机场才拨个电话跟Sam请辞,这事儿让Sam非常恼火。然而传奇的是,差不多一年以后,小马哥又回来了,而Sam竟然没事儿一样又接受了他。这事儿在我们这群Sam的中国员工里,甚至在Iquique的华人圈子以及圣地亚哥的一些社交圈里,都引起了好一阵波澜。虽然不乏诸如大肚能容、爱才之类的赞美,但更多的声音却是直言Sam像个傻逼,甚至有人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地断言他是个同性恋。就为这事儿,Leo还曾跟一个宁波商人干了一架,那个长了一口东倒西歪的牙齿的义乌老板在一次聚会中喝多了,拉着Leo不停追问有关Sam的种种传言,提到Maricon一词的时候,Leo瞬间把他按倒在地饱以一顿老拳。这事儿一开始闹得很僵,义乌老板因为在众目睽睽下被打了一顿,面子很挂不住,先是在众人劝阻的情况下咬牙切齿滴要把Leo剁成肉泥,然后又扬言要报警——好玩的是,当他说出要报警,拉着他的三两个同胞反而把手给松开了,那意思无疑就是说,与其报警,你不如现在去跟他打一架算了。没有谁愿意把这种事情摆到警局的台面上来处理。当然一口坏牙的义乌老板并不明白这其中的缘故,所以事情就变得多少有点两败俱伤了:Leo因为这事儿被罚了几千块美金的医药费,更糟糕的是正在申请的永久居留权被冻结了,即便后来跟智利人结婚,也没有能马上解除冻结,至今都还是每年一签的工作签证;而坏牙义乌老板则不断地被举报,无证驾驶、偷逃税、进口货柜夹带违禁品……最终在苦苦支撑了两年后,彻底离开了保税区。这件事的背后是一个大家都默认并尽可能遵守的规矩,那就是在中国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最好是在中国人自己内部解决,牵扯到圈子以外,是相当可鄙的行为,必定会受到全体中国人的排斥。 我从河边拐进一条小街,迎面就碰上了正用手推车推着一车货的Seba,他还是像过去一样,一丛用发胶精心梳理的莫西干发式从脑门一直延伸到后脑勺,除此之外整个脑袋都剃得光溜溜,一年多不见,肉嘟嘟的圆脸长了不少胡须,胳膊上有多了俩纹身。这个20出头的少年,拥有着不可多得的足球天赋,从10岁起就作为智利大学少年梯队的明星频繁被媒体曝光,如果不是那该死的伤病,他完全有机会在18岁前登上一线队的联赛赛场。在等级界限分明的圣地亚哥,以及所有的拉美城市,足球几乎就是贫民少年改变命运脱胎换骨的唯一途径,还没断奶就被老爹抛弃的SebastianSalas也一样。所以当他因为太多的伤病而被球队清理出门,他所受到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下这样两条路子:要么拿球队打发他的那点钱去上学,要么找个工作。Seba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整个少年时代就没怎么好好读过书,并且他刚有了一个儿子。所以还没满18岁的SebastianSalas,没有成为第二个Marcelo,却成了第一个到Sam的圣地亚哥公司的第一个仓库工。 Seba有点不高兴,年轻的小孩总爱把心情放在脸上,但看到拦住去路的人是我,他就高兴起来了,咧着嘴笑呵呵地问怎么会是你。我俩站在街边抽烟,他给我看钱包里儿子的照片,“下个星期就过生日了,4岁。”他说,“你要在圣地亚哥呆多久啊,一起来给儿子过生日吧。”我说,我现在还说不准要呆几天,因为完全不知道英国大使馆那边多久可以批下签证,如果时间快我就能留在圣地亚哥等,如果时间慢我就得先回去。他点点头表示赞同,在圣地亚哥要住个像样的酒店花费可不便宜,“不过你为啥不住在公司里呢?和马一起。”他说。 “靠!那还不如跟你一起住,是吧。”我笑着说。 “是啊,他这个问题狂人,浑身上下每根毛都是毛病。”他说,“最近他越来越烦人了,你知道,他从不叫我Sebastian,我感觉他就是故意的,非要让我不痛快。Lucianoven,Lucianono,Lucianomalo我真的很不高兴。喔,你看,”他突然转开话题,“那边,多他妈结实的两条腿,夏天真他妈好!”他撅起嘴吹了两声口哨,街对面沿着河岸走的女孩子扭头到处看,他开心的笑起来。等笑声落下,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打算不干了。 “为啥,就因为你的头儿不叫你Sebastian?”我知道他为啥不高兴。他身份证的第一个名字是Luciano,和他老爸一个名。老Luciano大半辈子人都混在澳大利亚做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为生,某一年回到圣地亚哥,遇到Seba的妈妈,两人热情似火滴过了几个月后,怀上了Seba。说不清是什么样的鬼使神差,这个闲游浪荡的家伙竟然决心要做一个合格的爸爸,并且据说还真的是做的非常不错,以至于年仅17的Sebastian的妈妈经常会在睡梦中甜蜜的醒来。好景不长的是还没等到儿子长牙呢,老Luciano就彻底的厌恶了平静的家庭生活,在一个阴雨蒙蒙的7月初的早晨,年轻的妈妈被孩子的哭声吵醒,发现身边的男人已经不见。老Luciano又回到了澳大利亚过着从前的生活,不定时的,有时三两个月,有时一年多,老Luciano会邮点钱给Seba的妈妈,但再也没有出现在他们母子俩的生活中。“我痛恨这老混蛋!”Seba不止一次地说过。 “我想去做海员,可以多挣点钱。”他说,“我还要活好几十年呢,我不想总是跟一大堆纸箱子混在一起。” “那是,谁也不会这样想。”我附和着说。 “周围都是大海,不管从船头还是船尾望过去,看不见岸,船长一声令下,你就得玩命的干活……到了晚上,喝朗姆酒……”Seba像是在跟我说,又像是已经梦游到了海上,他把头昂起来,将嘴里的烟努力地喷向天空。我不得不提醒他,现在已经是21世纪,除了一些比赛用途的船之外,已经没有他描述的那种帆船在海上跑了,现在的海员,大部分时间得呆在甲板下面干活,并且,喝朗姆酒的机会一点也不会比在岸上多。 “那也没啥大不了,要知道那总归是在海上。”他说,抬脚踢了一下身边手推车上的箱子,“我得干活去了,晚上我一定要请你喝一杯。” 我们先拥抱再击拳,就此告别。 周三开讲周三不是星期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diyagea.com/sdygjc/7506.html
- 上一篇文章: 超震撼BBC纪录片蓝色星球全8集
- 下一篇文章: 香得扑鼻,辣得过瘾圣地亚哥香锅放大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