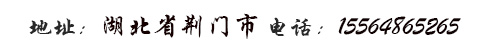采访手记黄仁宇印象
|
采访黄仁宇 年底我们《读书时间》节目组跟随一些出版社组团去美国采访拍摄,任务之一是拍一个黄仁宇先生的专辑,另一项目是采访《学习的革命》作者之一,珍妮特·沃斯。 我们先到了洛杉矶,参观了一个图书博览会,之后同行出版社的人都到迪士尼公园去玩了,我们则抓紧时间去圣地亚哥采访沃斯,之后便马不停蹄的赶往纽约准备采访黄先生。(有点遗憾,错过了那次机会到现在还没去过迪斯尼)因为在沟通采访事宜的时候我们得知黄仁宇先生的夫人患有癌症,马上要去纽约治疗,就等我们采访完后他们老两口就要动身就医,所以不能后延。 采访黄仁宇是我一直想做的选题,只是苦于他在美国,岁数大了出行不方便,这么多年从没回过大陆,所以只能等待机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学者散文开始流行。诸如“天一阁”“王道士”等文字在读者当中有很大影响和众多的追随者。看惯了“荔枝蜜”“茶花赋”的读者自然觉得余大师领风气之先,别开生面,纷纷叫绝“散文可以写得这么有历史味”。 不久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开始流行,那是因为他独特的叙事方法。在那本书的开头他这样写到——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间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这种文字现在看着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想想二十多年前那会儿,我们啥时读过这样的历史书!读者纷纷赞叹“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而且你会发现把历史书写得有散文味比把散文写的有历史味更难。 可以这样说,黄仁宇的历史著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受到读者青睐是正逢其时。 在这之前,由于受到那场政治风波的影响,思想界学界一片肃杀之气,死气沉沉。但小平同志南巡画的的一个圈,成功地把信任危机引到了一切向前看,既“向前”也“向钱”。商品大潮裹挟一切领域,人人都忙着赚钱,不几年人们的腰包有点鼓了,脑袋却空了。但历史大潮也透出一点缝隙,“仓禀实而知礼节”,社会上这时也明显地表露出强烈的阅读需求 就历史类的阅读来说,我们习惯了教科书千篇一律的框架式表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划分”“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奴隶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从小到大学到的就是这一套。一个冰冷的,人为设计好的框架,除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们,看不到有感情、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和事件。 所以当你看到黄先生的著作时一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黄仁宇家的小镇newpaltz 汽车出了纽约市沿着高速公路开了多英里,穿过了凡是读过黄仁宇先生著作都知道的那条著名的赫逊河,我们来到了纽帕尔茨(newpaltz)小镇,那是年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冬日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这个十分安静的小镇上,使这个远离喧嚣的地方更增加了一抹宜人的色彩。山清水秀,恬淡安逸,真是个养老的好地方。 主持人刘为和黄先生夫妇交谈 黄先生说,他曾多次接待香港台湾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新闻记者,不过来自祖国内地的记者采访,还是第一次,这也让我们有点与有荣焉的赶脚。 黄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赫逊河,并且还以它做书名写下了一本学术著作《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想来他用这个做书名字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地理位置,这是他的家。第二层意思可能深奥点,就是远观、远距离观察会有“不在此山中”的那种清醒或者超然,可以摆脱圈子里的人情关系、学术派别以及政治氛围,写起来少一些干扰,少一些顾虑。现实确实是这样,很多时候“不识庐山真面目”,困在里面怎么能看得清呢! 黄先生的书在国内畅销了二十多年,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读者看了都说好。这几年开始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觉得对他的评价是不是太高了。历史学上的争论很正常,专业的学术观点分歧其实也不太干我们普通读者的事,我这里主要想写写不到三个小时的采访,面前的这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和数年以后越来越清晰的感觉。 黄先生家的客厅不太大,屋子四处都摆放着书。一侧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手书条幅“乐天长寿”,我刚要大惊小怪,黄先生赶紧说“那不是真品”,语气自然平和。居中一组沙发,墙壁上方悬一镜框,内镶横幅“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书法遒劲有力,没注意是何人所书。查此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出自《金刚经》。“住”指的是人对世俗、对物质的留恋度;“心”指的是人对佛理禅义的领悟。大意是说人应该对世俗物质无所执着,才有可能深刻领悟佛法。 黄先生个子不高,短短的一头白发,深色的眼镜衬在白皙的皮肤,一看就是个做学问的模样,很合那横幅蕴寓的意境。 寒暄过后便开始了我们的采访。黄先生首先从自身的简历谈起,从军的经历,后来进入大学,半路出家开始钻研历史,写书的初衷和过程,从《万历十五年》谈起,逐次谈及《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并涉及到中国的改革和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谈及具体的历史问题当然比较枯燥,黄先生差不多把他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重点又复述了一遍,这些都没给我留下更多的回味。整个采访我觉得只有两点可重点说一下。 其一,黄仁宇的书中有一条很特殊的表述,他多次提到“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这是我从没在其他历史书中见过的说法。所以我们肯定要当面请教一下如何理解这个概念。黄老这样解释道—— “管制人类的方法基本上只有三个,第一个的是精神上的激劝,像牧师、政治指导员,鼓励人民为善;第二个方法是武力强迫你就范,警察诠释这个条例是怎么样的,你违反了法就要惩办;第三个方法就是激励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然后造成一个系统,每个人彼此都互相竞争又互相合作。所以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只管你是不是合法或者非法,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这种办法就是变成一个全面货币管制的办法。全面的货币管制就是工资、财政、税收、公债、私人的交易经理、法律,全部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我的理解就是要有一个量化标准,一切用数字说话。类似现在所谓的“大数据”吧。 其二,还有一段采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对我以后的阅读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黄仁宇先生特别强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无所谓他对错无所谓他好坏,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站在一个高度说明,为什么在那个时间段在那个地方会出现那样的人,这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作用是怎样的,他给后世带来的影响是怎样的。不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不同的时间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一样,这都是正常。 同事熊文平摄像,我就拿个反光板 整个采访历经两个多小时,主持人刘为提问,我的同事熊文平负责摄像,我则拿一个反光板在需要的地方补一点光,所以我能够比较清晰的观察到整个场景。 黄先生坐在沙发上,但他不是后仰着将身体陷在沙发里,而是自始至终地将身体前倾,保持着仔细聆听的态度,用一种很尊敬对方的身体语言同我们交谈。我看得出来他这样长时间坐在沙发上将身体前倾是很吃力的,以至于他不得不用右手支撑在身体右后方,这使我有点感动。采访结束时黄先生对我们说,他的妻子得了癌症前景渺茫,能不能请她也讲几句,让她开开心,这又使我感动了一次,真乃谦谦君子之风度。黄先生对夫人评价很高,因为夫人是他每一部著作的第一读者。我们当然满足了他的心愿。我想黄夫人大概不知道他的先生黄仁宇在中国学界有多大的知名度。 ? 临告别时黄先生把我们带去的书和他赠给我们的新出版的书《新时代的历史观》认真地签上名送给我们。 节目在央视《读书时间》播出后观众反应非常强列,不久我们接到了黄仁宇先生从美国寄来的信,字迹工整娟秀,配以黄先生专用的私人信笺,风格清新,看得出很认真的。 黄仁宇先生在信中很高兴的告诉我们,看了节目以后他非常高兴,很多在国内多年不见的朋友,也是通过这个节目看到了他并跟他取得了联系。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的一个朋友上次见面还是在六十年前,还是在西安事变时,这次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见到了他,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 黄先生手札 遗憾的是才过了一年多,年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了黄先生去世的消息真让我吃惊不小。黄夫人的癌症治疗得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但黄先生这么快就去世了,还真是心里有点堵得慌。 从美国回来后就陷入些事务性工作中,当年《读库》立宪约我写一篇采访记也因为静不下心来一直没动笔,还有就是刊物比较正规有学术规范,我们这种随感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能凑合着发一下朋友圈,熟人之间看看罢了,所以一放就是二十多年。 文中的几张照片都是当年采访时匆忙拍摄的,配上文字留个纪念吧!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diyagea.com/sdygjc/8421.html
- 上一篇文章: Kindle时刻
- 下一篇文章: 出道爆红遇车祸hellip事业巅峰再